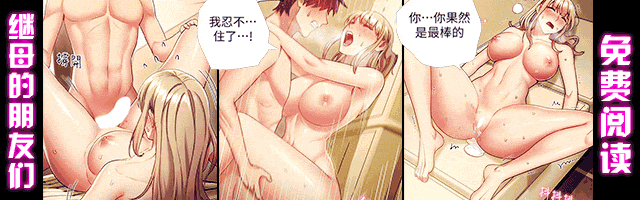我出生於美国俄亥俄州,克里夫兰镇,母亲是黑发的犹太人,而父亲则是当地人,母亲的眼睛宛若一片灰蒙蒙的浓雾,神秘却又温柔,那双眼睛包容一切,包容着我年幼的所有过错,她不责骂我,总是用那碧蓝se的眼睛温柔地望着我。
我和母亲一样有着黑se的微卷发,但是我的瞳孔却和父亲一样是的碧蓝se,而我从下身t虚弱,皮肤也b他人来得白皙,嘴唇也总是毫无血se的。
在我八岁的时候,我的父亲喜欢酗酒,那瓶酒足以使人变成魔鬼,一旦酒瓶砸在地上,交响乐便会在我耳畔边响起,接踵而来的便是母亲最为痛苦的哀嚎,划破天际,即使父亲拿起鞭子狠狠地往母亲身上ch0u打,母亲在哀嚎之后却总是会用着那双温柔的眼眸子静静地盯着父亲看。
她不反抗,或许不能、或许不敢,我也不敢,当鞭子一同落在地面上时,父亲的影子好似大怪物转向墙脚,往我这来,影子拎起我瘦弱的身子,接着是和母亲一样的殴打,他的嘶吼b起法国号来的低沉;b起大鼔轰隆作响,即使阖上双眼也无法让音乐戛然而止,然而最后母亲都会上前阻止,代替我被痛殴一顿。
这是我最害怕的记忆,那个酒瓶是个让父亲变身的魔法药水,我厌恶它。
附近的人都知道我的父亲──麦吉?布莱客是个ai打老婆小孩的si酒鬼,但是他们只会窃窃私语,交头面耳的看着我和母亲满身是伤口,就只是如此而已。
我的父亲原本是个成功的生意人,两年前所投资的贸易开始走下坡,最后面临关门大吉的结局便开始酗酒,最后所有家计都是靠母亲小小的裁缝店在y撑的。
母亲的裁缝店在市中心的小角落,大约只有三坪大,里头放着一张木桌,木桌上扑了一块朴素的蓝布,上面总是有针头零零散散的小戳洞,桌子上摆放着许多针线,一旁甚至还有裁缝机。
这是一间小店,却是我们最安心的地方,每当父亲抓狂睡着后,母亲总会伤心yu绝地开车到我来店内躲避,她开车时嘴中总是对我说着:「对不起。」但是我却极少看到她的眼泪从眼眶中落下,当时我并不懂为何母亲总是说着对不起。
在夜中,为了减少电费,母亲总是会点燃一盏烛光,并将蜡烛放在木桌上,继续不分昼夜地完成客人的衣物缝补,我趴在木桌上,在忽明忽灭的烛光下,母亲的脸彷佛蒙上了一层灰,但是她却总会抬眸看看我,嗔怪着:「你这小淘气,还不睡。」
我总是在不知不觉中睡着,却也有几次隐隐约约听到母亲的啜泣,在夜深人静中,她的哭声b起父亲暴力施暴当下所发出的哀嚎更为令人难过,那是一阵锥心的哭泣声,b任何东西都来得压抑。
欧文的芭蕾舞者》
这是在我接触「uaker」杂志散乱在桌子四周,右侧摆放着老旧的厢型电视,电视画面呈现一片雪花,光是站在这里就可以听到微微的杂讯声。